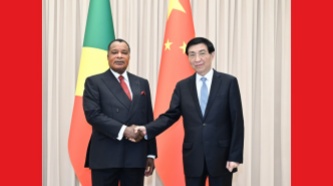中国政协网www.cppcc.gov.cn
首页>委员风采
守得雪莲朵朵开——记全国政协委员明吉措姆

明吉措姆
全国政协委员、西藏藏医药大学藏医系教授、珠峰领军人才、中国西藏文化保护与发展协会常务理事、藏研中心国家高端智库学委会委员、WTO ISO国际标准化注册专家。
初春的羌塘草原,风似淬了沙的刀。强光混着碎砾石砸在17岁的明吉措姆脸上,那感觉不是疼,是密匝匝的麻,像无数只细蚁在啃噬脸颊,没一会儿,就洇出淡红的印子。
藏袍的下摆被风灌得如绷紧的帆,每一次涌动,都把她往马下扯拉。马背上的明吉措姆紧紧拽着简陋的药箱。没一会儿,马儿的呼吸也开始沉重起来——它也累了,从日出到日头偏西,整整8个小时路程,连停下来啃草的功夫都没有。
“走了走了。”想到牧民们在帐篷外翘首等待,明吉措姆咬牙拍了拍马背,朝着高原深处前行。马背上的她还不知道,自己将走过聂荣县的荒原、走过牛津大学的讲堂、走过全国政协的会场。她只知道,此刻掌心的疼、腰背的酸、喉咙的干,都抵不过牧民们企盼的眼神。
从草原到国际:为藏医药寻“现代语言”
1988年的聂荣县还没有水龙头,取水要靠扁担挑;没有通畅的公路,行医全凭骑马;药少得可怜,遇到重症病人,只能自掏腰包买药,有时,还需亲手制药。
“那段日子,我见过太多被病痛困住的牧民。大家把100%的信任交给我,我绝对不能辜负。”藏医的《四部医典》里藏着千年智慧,许多疗法能够有效缓解各种疑难杂症,可明吉措姆发现,这还远远不够。“这些宝贵的理论和实践不能仅仅局限于让周边群众受益,还需要经过科学的研究和验证,推向世界。”
这种愿望,成了明吉措姆求学之路的起点。她先是考取藏医大专,又攻读藏医硕士。可随着对藏医理解的加深,她愈发意识到,要让藏医药走出高原,必须掌握“现代科学的语言”。于是,她做出了一个决定——出国深造。
2000年初,明吉措姆踏上留学之路,攻读医学人类学博士学位。为了强化科研能力,读博期间她还申请了谢菲尔德大学的公共卫生硕士,后来还加入牛津大学循证医学中心心脑血管研究团队。
“留学时,几乎没有任何时间休息。”清晨的台灯下,明吉措姆习惯性摸向桌边,想端起阿妈常递来的酥油茶,指尖触到的却是咖啡杯。有人劝她“没必要这么拼”,她却总提起家乡那些等着治病的牧民:“如果我多学一点,就能多救一个人!”
在牛津大学从事研究期间,明吉措姆经历了一次尤为珍贵的学术交流。她的导师是人类学领域的权威学者。在一次探讨中,导师从严谨的学术规范出发,指出藏医药领域仍需更多实证数据的支持。明吉措姆将自己长期积累的案例与初步观察结果细致整理,以谦逊但坚定的态度,与导师进行了长达3天的深入讨论。
“我不是要否定现代科学,而是想证明我们藏医药的价值。”明吉措姆对导师说,“藏医是我们祖先用千年实践总结的智慧,不能因为‘不符合现有框架’就被否定。我们应该用科学的方法验证它,而不是改造它。”最终,导师被她的坚持打动。
在国外的11年里,明吉措姆的脚步遍布20多个国家,踏足世界各地大学讲学,参加组织高端学术交流研讨会,促进了藏医药学的国际化发展。同时,她也拥有了大量国外患者,他们通过藏医的调理重获健康后,握着明吉措姆的手说:“我们真怕你哪天不来了。”
牛津大学曾向她抛出橄榄枝,邀请她担任资深研究员;奥地利科学院邀请她担任终身制研究员。朋友劝她留在国外能有更好的发展,她却摇了摇头说:“只有回到西藏,我才能真正把藏医的根扎深。”
2016年,明吉措姆带着多年所学,回到了西藏藏医药大学。那片她魂牵梦萦的雪原,终于等到了她。
从校园到政协:为藏医药破“发展瓶颈”
回国后,明吉措姆同样面对种种挑战。团队协作、研究平台和研究氛围的限制,使得许多项目的推进并不容易。
“最难的不是缺乏资源,而是缺少合力。”明吉措姆尝试组建团队,却注意到医学理论与应用之间普遍存在差距。在申请科研资金时,因项目较为前沿,评审专家对其可行性提出了疑问。
明吉措姆没有放弃。她从自己的学生入手,带学生一起去基层收集案例;她主动对接西藏多家医院,把自己的研究数据分享给临床医生;她甚至组织学生翻译国外藏医药重要文献,打开国际视野。
转机出现在明吉措姆成为第十四届全国政协委员后。“政协这个平台给了我更多发声的机会。”明吉措姆格外珍惜这份责任,刚参加完全国政协会议,就提交了《关于推动藏医药国际化人才培养的提案》。她在提案里这样写道:“当前全球对传统医学的关注度越来越高,我们藏医该抓住这个机会。建议在西藏藏医药大学设立留学生院,逐步吸引外国学生,让他们成为藏医国际化的‘桥梁’。”
这件提案很快得到重视,可在推进过程中遇到“卡点”——西藏藏医药大学未被列入国际大学名单,无法招收国际学生。明吉措姆希望引起有关部门重视,加快补齐学校国际名录申报的基础短板。“现在留学生院的筹备虽然慢,但至少在往前走。”说起这件事,她脸上露出了欣慰的笑容。
作为政协委员,明吉措姆的调研脚步遍布西藏的山山水水,每到一处,都要仔细询问“藏药的储备够不够”“牧民看病方便不方便”。今年6月赴广西调研时,看到壮医、瑶医与现代医疗融合服务群众的场景,明吉措姆深受触动:“各民族医药智慧互鉴,才让藏医药既能守住《四部医典》的根,又能接上时代的脉。”
“今年是西藏自治区成立60周年,我亲眼见证了藏医药的‘蝶变’。”明吉措姆感慨地说,从过去的“家族式传承”到现在的“高校教育”,西藏藏医药大学已经培养了上万名藏医人才;从过去的“缺医少药”到现在的“73个县中有40多个成立了藏医院”,藏医医疗服务实现了“全覆盖”;从过去的“手工制药”到现在的“现代化生产线”,西藏的藏药企业已经成为支柱产业。
“我们还有很长的路要走。”明吉措姆的眼神里满是坚定。
从孤身到团队:为藏医药绘“未来蓝图”
如今的明吉措姆,日程表总是排得满满当当,有人问她“累不累”,她笑着说:“只要能做实事,就不觉得累。”
明吉措姆现在最看重的,是高原医学领域“藏医药重大优势病种研究团队”的建设。“西藏是世界上海拔最高的地区,高原病是世界级的医学难题,而藏医有千年的应对经验。”明吉措姆和团队已经梳理出多种藏医治疗高原病的经典方剂,通过现代药理研究,发现其中的多种成分能有效改善高原缺氧引起的心肌损伤、肺功能下降。“如果能建立专门的研究中心,我们就能进一步验证这些方剂的疗效,甚至研发出新的药物,不仅能造福西藏牧民,还能为全球高原病治疗贡献‘中国方案’。”
为了这个目标,明吉措姆一次次去自治区科技厅、卫生健康委等部门沟通,争取政策和资金支持;她对接国内的顶尖医学院,邀请专家加入团队;她还带着学生去日喀则海拔5000米以上的地方,收集高原病患者的临床数据。“我有100%的信心,只要平台建起来,一定能出成果。”
在明吉措姆看来,藏医药的未来,既要守根,也要创新。守根就是要保护好藏医的传统理论和文化,不能让《四部医典》的智慧被遗忘;创新就是要用现代科学的方法解读藏医,让藏医能融入现代医疗体系。“比如藏药的‘药食同源’,红景天就是很好的例子,既能入药,又能做保健品,如果能做好产业化开发,不仅能带动西藏的经济发展,还能让更多人了解藏医。”
明吉措姆也格外关注女性在藏医领域的发展。“过去藏医多是男性传承,现在越来越多的女性加入进来。”她带的博士生里,女性占比很高,她常对学生说:“不要觉得女性做科研不容易,只要有初心、肯坚持,就能做出成绩。”
工作得闲时,明吉措姆喜欢在西藏藏医药大学的校园里,看那些来来往往的学生。他们有的在讨论《四部医典》,有的在实验室里做药理实验,有的准备去基层开展实习义诊。看着他们,明吉措姆总能想起17岁的自己,想起那匹在羌塘草原上驮着药箱的马。“那时我只是想做个好医生,没想到能走到今天。”她说,“藏医药的发展,不是我一个人的事,是一代又一代人的事。我会继续做铺路石,让更多年轻人能带着藏医走出高原、走向世界。”
问初心为何依旧滚烫?采访最后,明吉措姆做了这样的比喻:“我是守着雪域的一名普通藏医,就像那高原上的雪莲,不贪暖阳、不慕繁花,只为在家乡的土地上,把藏医的暖意、把祖先的智慧,递到每一个盼着健康的人手里。”(记者 王晶 韩雪 王亦凡 李京 宋宝刚 汪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