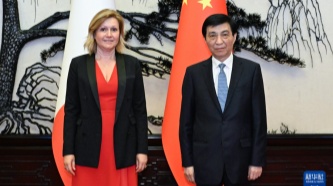中国政协网www.cppcc.gov.cn
首页>委员风采
耕耘天地间——记全国政协委员闵庆文

闵庆文在贵州从江小黄村考察稻鱼鸭系统。 (图片由受访者提供)
闵庆文:第十三、十四届全国政协委员,北京市政协常委,九三学社中央资源环境专门委员会副主任、北京市委会副主委,中国科学院地理科学与资源研究所研究员、自然与文化遗产研究中心副主任。获“全球重要农业文化遗产特别贡献奖”“全国创新争先奖状”和“全国优秀科技工作者”称号。
2005年6月,浙江青田龙现村。村民伍丽贞推开家门,撞见了几位来自“山外边”的陌生人。其中的一个裤脚沾满泥点,头发花白,一张被太阳晒得发红的脸却笑得舒展,正是闵庆文。
“这几位是联合国和北京来的专家,他们来考察咱们的‘遗产’!”村干部介绍道。村民聚拢过来,质疑声却几乎凝固了空气:“什么‘遗产’?莫不是来骗人的?”
这场始于2005年的初遇,拉开了中国农业文化遗产保护的序幕。
“黑暗中的出路”
2003年,在联合国粮农组织(FAO)启动全球重要农业文化遗产保护试点后不久,我国积极参与其中,并开始了浙江青田稻鱼共生系统申报首批保护试点工作。彼时,农业文化遗产尚是一个全新概念,保护更无经验可循。FAO仅划出方向:“由各国自己摸索。”
闵庆文在著名生态学家李文华院士的推荐下,接下了这个“在黑暗中寻找出路”的挑战,来到了浙江青田龙现村进行考察。
“那时连‘农业文化遗产’是什么都还不是很清楚,更别提如何保护了。”闵庆文回忆道。当他试图向村民解释“祖辈的稻田养鱼方式是宝贵遗产”时,回应他的是直白的怀疑:“我们祖祖辈辈就是种稻养鱼,怎么就是遗产了呢?”
面对质疑以及“没有经验、没有经费、没有团队”的窘境,闵庆文将目光落点在龙现村的历史纵深。“1000多年前,你们的祖辈就在这里依山造田,修渠引泉。田里种稻,稻下养鱼,鱼食杂草害虫,鱼粪反哺稻田,既得米香,又添鱼鲜。这是山民的生存智慧,对现在和未来的农业发展意义重大。”
稻鱼共生蕴含的生态智慧让闵庆文着迷,他思考更多的则是在现代化背景下如何让这些宝贵的农业文化遗产保护下来、传承下去。两年多时间里,他带领学生多次深入青田乡间,入户调查、收集数据、评估价值、编制规划……他们试图厘清三件事:现状如何?价值何在?如何保护?
“稻田养鱼在我国已有2000多年历史,南方许多地区都有,为何青田能成为代表呢?”闵庆文的解释切中要害,“青田不仅有持续1300年的实践,还保有传统水稻品种和后来被列为国家地理标志产品的青田田鱼,还形成了深厚的文化习俗:建房先挖鱼塘,嫁女鲤鱼作妆,逢年过节必舞的鱼灯舞入选国家级非遗。”在他看来,正是这些“活态”的生态模式、物种资源、技术体系、文化习俗和景观结构,共同构成了系统性的农业文化遗产。
科学认证只是起点,活态传承才是考验。2008年底,青田稻鱼共生系统成功成为FAO牵头的全球环境基金项目试点。闵庆文带领团队在青田进行了为期5年的保护与发展探索,推动龙现村打出“农遗牌”:鼓励农民坚持传统种养,发展有文化内涵的生态农产品,发展农文旅融合新模式。
这一次,变化来得比稻苗抽穗更快。伍丽贞家率先挂起“渔家乐”招牌,游客挤满小院。“靠这营生,我家盖起了五层楼,还新添了辆汽车!”她兴奋地拉着闵庆文参观新房。米、鱼、鱼干价格攀升,龙现村声名鹊起。曾经寂静的山沟,晨雾中开始回荡导游的解说:“各位请看,这就是全球重要农业文化遗产核心区……”
青田稻鱼共生系统的成功经验如同一枚投入湖面的石子,涟漪扩散到更远的山野,也荡开了闵庆文对农业文化遗产保护路径的深层思考。
“到底什么是农业文化遗产?一提到这个词,大多数人或许会想到古稻田遗址、出土的农具等等,但这些都不是我们今天所说的农业文化遗产。”他加重了语气:“其最显著的特征在于它是‘活着的’有机体,而非陈列在博物馆的标本。”
动态保护的辩证法
青田稻鱼共生系统的成功并未让闵庆文停下脚步。他的目光旋即投向更远的山野——云南红河的哈尼梯田、普洱的古茶园,贵州从江的稻鱼鸭……面对时代变迁下传统农业的式微,闵庆文洞察到关键:“传统农业在挤压中求生存,一味追求‘原汁原味’的冷冻式保存终将窒息其生命。唯有让传统智慧融入现代生活,实现可持续发展,才是真正的保护。”
2010年,闵庆文创新性地提出“农业文化遗产动态保护理论”,开启了传统农业与现代社会融合发展的探索,其精髓在于精准把握“变与不变”的辩证法则。
这一理论在浙江湖州的荻港村找到了生动注脚。2014年,闵庆文走进拥有2500多年历史的村落。“桑基鱼塘系统有着‘塘中养鱼、塘基种桑、桑叶喂蚕、蚕沙养鱼、鱼粪肥塘、塘泥壅桑’的循环体系,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誉为‘世间少有美景,良性循环典范’,却因桑蚕产业转移而日渐沉寂。”
在闵庆文等专家的引导下,村民们主动拓展传统农业系统的多种功能与多元价值,蚕茧产量减少,但桑叶被制成清香的茶叶,蚕茧不仅用于制作精美的丝绸,还发展出了蚕茧画;古老的桑基鱼塘不仅依然产出农产品,更成为研学游的核心课堂,吸引着都市人前来体验生态循环农业的智慧。千亩桑基鱼塘的物理形态被完好保存,但其内在功能已悄然蜕变。
“为什么有人愿意到这儿休闲、研学?因为这儿拥有别的地方没有的独特东西。”闵庆文认为,保护、利用和发展农业文化遗产,关键在于充分发挥其在农产品供给、生态保护、文化传承等方面的多元价值,突出“农味”和“地方味”。
2017年,湖州桑基鱼塘系统被认定为全球重要农业文化遗产。申遗成功后的荻港,不仅守护了种桑养蚕养鱼的传统,更开拓了文创与文旅产业——遗产保护与经济发展在此实现了双赢。每年的鱼文化节,闵庆文都会到荻港与村民们相聚在一起,共同见证这份传统的延续与创新。2025年鱼文化节期间,走在曾来过无数次的蚬壳路上,他感慨万千:“20年的实践让我深刻认识到,必须建立多方参与机制,在动态保护中实现农业文化遗产的传承与发展。”
方法论已然清晰,但闵庆文的忧虑并未减轻。“中国是农业大国,随着自然条件的变化、社会经济的发展、科学技术的进步,延续数千年的农业传统面临着消失的危险,最为严重的是,随着城市化的发展,大批有知识的青年离开农田,传承出现断层。”
那么,谁来延续古老耕作?谁又能独守传统?闵庆文的看法务实而清醒:不刻意追求大而多,也无须普遍推广。但在地理偏僻、生态脆弱、不适合现代农业技术的地区,传统耕作方式往往最适合当地的自然条件,应当作为特殊的生态区域、文化区域进行适当保留。通过挖掘农业的多功能价值,发展特色产业,促进经济发展和农民增收,是可持续的保护之道。
出身苏北沛县农家的闵庆文,格外重视农民的作用。“农民是农业文化遗产的创造者,也是保护传承的主体。只有让农民真正受益,保护才能落到实处,让遗产保护和发展成果惠及更多农户。”
为了这个目标,20年里,闵庆文组建了涵盖多领域的研究队伍,足迹遍及大江南北,发掘农业文化遗产价值,推动产业融合发展,助力众多贫困县脱贫摘帽。而比起获得的科研奖励和荣誉,闵庆文更珍视内蒙古自治区敖汉旗的“小米产业发展功勋奖”、浙江省庆元县的“荣誉市民”和从江县小黄村村民委员会授予的“荣誉村民”称号——这些来自土地和人民的认可,被他郑重安放在办公室最显眼处。
土地和人民,始终是闵庆文力量的源泉。保护发展农业文化遗产,闵庆文认为,最深层的意义在于传承先人千百年总结的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思想、生态环境保护和资源循环利用的智慧,这才是遗产中的精华。
征途未竞
6月的阳光透过百叶窗,在中国科学院地理资源所那间堆满材料的办公室桌上投下斑驳光影。这扇门时常关着,因为它的主人总在田野间奔走。
“截至目前,世界上去过全球重要农业文化遗产地最多的人可能就是我。”带着学者特有的严谨,闵庆文列举了一组数字,“世界95处全球重要农业文化遗产地,我去了49处;中国的25处,我去了24处。另外,188项中国重要农业文化遗产,我去了84处。到一线去,把论文写在大地上,是我坚守的原则。”
自2018年成为全国政协委员以来,闵庆文一直都在为农业文化遗产保护鼓与呼。“中国不仅要保持全球重要农业文化遗产数量稳居世界领先地位,还要不断贡献‘中国智慧’和‘中国方案’。”随着农业文化遗产日益走入公众视野,年轻人也开始涌入。全国两会期间,“90后”少数民族界委员杨钰尼“以美育守护哈尼梯田文化”的呼吁等,正是闵庆文等先行者推动形成的共识回响。
在对农业文化遗产发掘与保护、国家公园与自然保护地体系建设等方面开展了系统调研后,闵庆文注意到大多数农业文化遗产地都处于重要生态功能区。如何充分发挥其蕴含的生态价值、发挥当地居民在生态保护中的作用,成了他近年履职的核心关切。为此,围绕这两大主题,他提交了10余件提案。
“2017年,我主持了一个国家重点研发计划项目——国家重要生态保护地生态功能协同提升与综合管控技术研究与示范,探索自然保护地生态与经济、文化协同提升的路径,并在三江源和神农架两个国家公园试点区进行应用示范。基于此,我提出建议,要建设有中国特色的国家公园。建设国家公园、保护生态环境要注重保障当地人的利益,注重保护国家公园的生态文化、民族文化和农耕文化。”闵庆文提出的这件提案被列为全国政协重点提案,具体建议在有关部门的相关工作里面得到体现。
越来越多的地方在积极申报中国重要农业文化遗产和全球重要农业文化遗产,越来越多的科研人员投入到农业文化遗产的保护与发展研究,越来越多的人到农业文化遗产地去观光、度假、研学……这片曾经沉默的土地,正发出日益响亮的回声。欣慰之余,闵庆文的步履未曾放缓——那些能让农业文化遗产焕发新生的科学路径,他依旧想在前、走在前。
晚风拂过稻浪的沙沙声,常将闵庆文带回苏北沛县的童年那些伴着蛙鸣入眠的夜晚。他知道,农业文化遗产不仅是历史的积淀,更是未来发展的启示。保护这些“活着的遗产”,最终是为了回答那些根本命题:人如何与自然共处?如何在时代发展的洪流中,守护那些让生命得以绵延的永恒智慧?
闵庆文的答案,没有停留在报告里。它依然需要在层叠的梯田上、在荡漾的鱼塘边、在农人舒展的笑脸中,一步一步耕耘出来。(记者 李京 杜晓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