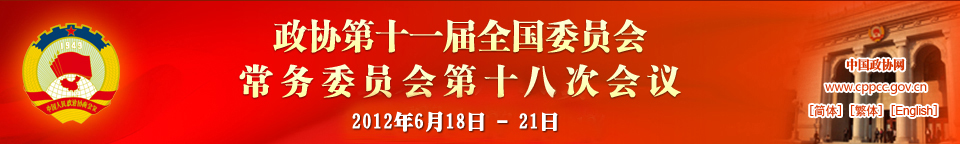
当前位置:专题首页 > 大会发言
致公党中央的发言
实施实体经济强国战略 推进实体产业迈上新台阶
中国政协网 www.cppcc.gov.cn 日期:2012-06-21
字号:[大][中][小] 打印本页 关闭窗口
2008年,波及世界的金融危机发生后,世界各国都在深入思考未来经济的发展问题。发达国家开始意识到,依靠无节制的消费,制造金融泡沫形成的经济发展方式存在巨大隐患,缺乏可持续发展能力。发展中国家也意识到,依靠资源和能源的过度消耗,依靠低端廉价劳动力形成的出口拉动型经济,同样没有可持续发展能力。美国、欧盟纷纷提出“再工业化”战略,以期弥补他们过去几年实体经济的缺失与不足,同时为了竞选,解决居高不下的失业率问题,加大了对实体产业的重视和投入力度,这势必对我国全球制造业大国的优势形成巨大的冲击和挑战。未来几年,我国一方面要加大以战略性新兴产业为代表的创新型产业的培育,另一方面,也要加大力度,不断稳固、提升我国传统实体产业经济的既得优势地位。
一、我国当前实体经济面临严峻的形势
随着全球经济危机的深度蔓延,我国实体经济面临的形势不容乐观,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外需市场大规模萎缩,严重影响“出口导向型”企业的需求。金融危机发生后,一方面,西方大量实体产业面临破产边缘,失业问题十分严重,倒逼西方发达国家的民众不得不转变消费观念,改变过去的超前消费和无节制消费的生活方式;另一方面,政府忌惮于大规模投资衍生通货膨胀等恶性循环,以及常年形成的财政赤字等问题,不敢轻易进行大规模投资。所有这一切,都必然深度影响我国实体产业的外在需求。
(二)国际产业竞争日趋激烈,对我国提升实体产业国际化能力构成严峻的考验。美国政府先后发布了《重振美国制造业政策框架》、《先进制造业伙伴(AMP)计划》;欧盟也推出了《欧盟2020》、《欧盟交通道路电动化路线图》等一系列“再工业化”的战略部署,他们一方面希望通过这些战略的实施,引导制造业回流,挤压我国实体经济的发展空间,另一方面,他们也在利用“碳排放”等环保标准对我国企业出口进行围追堵截。我国实体产业在此大背景下,要顺利保住固有订单,必然需要付出更多的代价。
(三)人口红利不复存在,劳动力成本上升让我国实体经济背上沉重包袱。随着我国进入人口老龄化阶段,年轻劳动力不足,社会养老等压力加大,劳动成本大幅提升,我国过去几年靠人口红利形成的低劳动成本优势将不复存在。劳动成本的上升传导至实体产业中,进而形成我国实体产业更大的负担。
另外,人民币升值问题、大宗商品价格长期居于高位波动、资源环境约束、缺少资金投入实体经济等问题也是影响当前我国实体经济问题运行的重要因素。
二、我国实体经济存在的主要问题
我国实体经济尽管在过去几十年的改革开放中得到了大幅提升,但内部结构不合理、创新能力低下等问题一直存在,具体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缺乏保护创新的产业环境,致使我国实体经济一直在低端徘徊。从我国出口结构来看,大多数还是以原材料的粗加工、低附加值的低端产品为主,甚至还有很多是简单的“代工”,赚取的是纯粹的“血汗工钱”。究其原因,一方面,企业前期创新投入高、周期长、风险大,后期知识产权得不到有效保护,随时面临“被山寨”的风险。另一方面,金融机构宁可投入房地产等暴利领域也不愿支持企业搞创新,特别是在提高银行存款准备金率后银行也无资金投入实体经济。长期累积下来,严重削弱了我国实体经济的创新能力。
(二)内需乏力,不能形成对我国实体经济的牵引能力。我国社会目前贫富分化趋于严重,对于富裕阶层来说,我国十分缺乏高端消费品,今年春节期间我国旅游者70多亿美元的奢侈品消费拉动的主要是西方国家的产业。而对于大多数工薪阶层和农民来说,囿于住房、子女教育、养老、医疗等方面的顾虑,消费只能维持在基本生活层面。高房价时期,一套住房几乎耗尽了相关几个家庭的消费能力,扼杀了内需消费的主力军。这种现象得不到改善,我国实体产业的内需找不到出路。
(三)缺乏国际知名产品和知名企业,这与我们大国的地位极不相称。对比日本数码产品的全球优势、德国装备业的精良品质和美国企业的创新能力,我国企业形成的知名品牌屈指可数,如何培育具有活力的国际知名企业和国际知名品牌产品是我们需要从深层次思考的问题。
(四)国企创新的积极性、主动性及投入不足;民企进入一些国企控制的垄断领域还存在“玻璃门”、“天花板”的问题,也严重阻碍了实体经济的发展。
三、建议
真正实现我国实体经济可持续发展,既要考虑当前如何稳固实体产业的自身优势,又要从长远出发,实施一系列推进行动计划。为此,我们建议:
(一)从国家层面,考虑研究实施“实体经济强国战略”,加强顶层规划,针对不同阶段、不同产业、国企和民企拿出实体产业振兴行动计划。
(二)加大财税政策改革和支持力度,推动实体产业发展。加快出台结构性调税政策,对暴利产业及领域提高税收,对实体行业减少税收。同时对于实体产业的科技创新、技改、升级实施一定的国家资金扶持。
(三)大力推进“两化融合”,以信息技术带动传统产业升级。加大力度,鼓励支持用信息技术改造传统产业,提升实体经济的生产效率及产品附加值。
(四)大力推进“产融结合”,鼓励企业做大做强。借鉴美国等西方发达国家产融结合的先进经验,把实体产业引导成为社会资本追逐投资的热点。建议成立以国家投资为引导、吸纳社会资本的千亿级的实体产业投资资金,扶持本国企业“走出去”,从而成为国际性知名大企业。
(五)大力发挥高校、协会、社会团体的作用,在知识产权保护、环境和标准研究、产业政策研究、行业发展指导等方面赋予更多的职责和权限。
(六)在国有企业绩效考核中,加大科技创新业绩考核力度,从而促进国有企业创新的活力和积极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