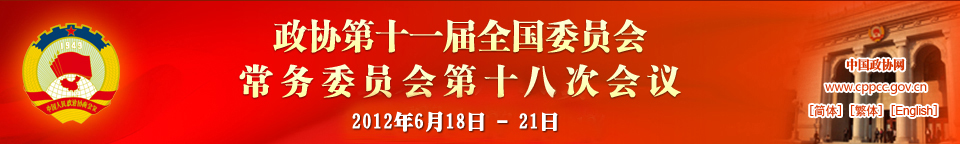
当前位置:专题首页 > 大会发言
赖明常委代表九三学社中央的发言
稳中求进积极稳妥地推进城镇化发展
中国政协网 www.cppcc.gov.cn 日期:2012-06-21
字号:[大][中][小] 打印本页 关闭窗口
目前,我国正处于城镇化发展的重大战略机遇期,虽然名义上城镇化率已达51%(实际仅35%左右),但与新兴发展中国家的60%,发达国家的80%,以及各方基本形成共识的中国期望城镇化率70%左右相比仍有很大发展空间。积极稳妥地推动城镇化,将为未来几十年中国经济发展提供持续动力,对于调结构、转方式、稳增长、促民生、保稳定,改变外向型经济难以为继的现状,实现稳中求进意义重大。
首先,从消费和投资两方面拉动内需。目前城乡居民消费比例约为31,城镇化水平每提高1%,将拉动最终消费增长约2%;同时,据我们的调研,每转移一个农民进入农村新型社区就需直接投入约10万元,并可带动2.2倍的其他投资,若城镇化率每年提高1%,则年新增投资至少4.3万亿元,相当于2011年GDP的9.2%。其次,节约资源,提高投入效率。我国农民平均十年建一次房,每年仅建房投入按现价计算近万亿元。宅基地每年以1%的速度增加,但1/4的住房长期空置,浪费巨大;同时,由于多年来农村人口流动加速,农村危房改造、村村通、沼气建设等投入效率也随之下降。城镇化发展可减少重复建设,实现一次建设长期使用。再次,推动农业生产方式和农民生活方式转变,有利于生态环境保护。据统计,农村面源污染在各类环境污染中的比重占30%—60%。在分散、低效的传统生产生活方式下解决农业面源污染耗费巨大。城镇化则有利于将垃圾收转、污水处理等功能集中,减少生活污染;通过土地流转改变农业经营方式,推动如设施农业、高效农业等现代农业发展,为科学合理利用农业生产资料,从源头上控制和减少污染奠定基础。
当前,我国城镇化存在一些值得重视的问题。
一是缺乏战略思维。一些地方不顾实际情况,忽视自身经济条件、资源禀赋、文化风俗、产业发展等因素,城市扩展贪大求洋、大拆大建,盲目撤村并居、“赶农民上楼”,等等。为此建议,要集中力量就城镇化的一些重大战略问题,以及各地城镇化的经验作进一步研究,分析不同地区的城镇化途径,因地制宜地推进城镇化科学发展。
二是城乡规划不科学、不合理,缺乏长远性、全局性。受到GDP政绩观驱动,各类规划朝令夕改;一些地方在编制规划时过于强调自身发展,忽视国家战略和区域发展统筹,同质竞争严重。不少规划未能体现可持续性和宜居性,导致“城市病”加剧。为此建议,加强生态文明建设,优化城镇布局,将资源集约利用、城镇可持续发展和宜居性相协调;完善规划执行监督机制,强化规划专家权责。
三是面临一些深层次制度障碍。如集体土地、农民住房“还权赋能”未能落实到位,抵押和买卖这两项最重要的“能”难以突破;又如二元体制下的户籍和社会保障制度,限制了农民真正融入城市,导致土地城市化速度高于人口城市化。为此建议,大城市加强和改进人口管理,中小城市和小城镇根据实际放宽落户条件,从制度上保护进城农民权益,扩大基本公共服务覆盖面,有序引导有条件的农民进城落户。
四是财政投入多头管辖、项目分散、效率低下。由于地方没有自主整合项目资金的权限,无力扭转“撒胡椒面”式的低效财政投入局面。同时,下级政府为获得项目资金,往往把精力用在“跑部钱进”上,造成公款吃喝屡禁不止,并增强了相关部门和个人的寻租冲动。为此建议,深化财税体制改革,提高一般性转移支付比例,强化地方特别是市、县一级整合使用各类资金的自主权,提升涉农投入效率。
五是产业发展水平亟待提升。一些地方在城镇化过程中虽然建立了产业园,但行业不集中、关联性不强、主导产业规模小、产业链短,多数仍然处于价值链下游,难以形成集群效应,易受外部冲击影响。为此建议,借助产业扩散,优化产业布局,以中小城市和城镇为产业转移重点,加强产业对城镇化发展的支撑;同时,完善农村金融体系,激活相关涉农产业,增强农村的经济活力。
